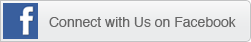Tribute Wall
Plant a tree in memory of Hong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ption
Provide comfort for the family by sending flowers or planting a tree in memory of Hong Xu.
Guaranteed hand delivery by a local florist
Loading...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61/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7/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9/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5/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3/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1/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9/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7/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3/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7/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1/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5/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3/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9/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1/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5/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9/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5/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7/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8/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60/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6/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4/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0/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52/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8/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2/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4/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3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6/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40/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6/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0/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2/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8/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34/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4/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8/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2
The family of Hong Xu uploaded a photo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tribute-images/5626/Ultra/Hong-Xu.jpg

Please wait
J
Jiang,wali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February 5, 2015
许红:
你好。从你父母那得知你4月16号开始放疗。目前你的放疗已进行了1个多星期,身体的反应强烈吗?
你4月16日寄到北京的片子,于4月23日问诊时听取了天坛医院孙彦辉大夫意见。孙大夫一改往常乐观的态度,认为片子显示了多点播散,近期病情进展加快。他认同目前实施第二次放疗,提示注意观察病情。他提及对于母胶质瘤而言,发现后生存的中位期是14个月。并提示注意前额病灶的症状,不宜一个人独处家中,需要有人看护,注意癫痫病的出现。普华医院的韩小弟大夫的门诊还未约上。4月23日他做了一天的手术。目前在争取5月4-6日能听听韩大夫的意见。
许红,你近期的病情加速进展,现实十分残酷。但需要冷静面对。一是加强治疗,一是调整情绪。面对这种高级别的肿瘤,你在手术后已经争取了有生活质量的25个月的时间。目前仍有继续争取的可能。一句英语谚语说得好: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believe. Better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are patient and the best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don't give up. (好的事情发生在相信的人身上,更好的事情发生在耐心的人身上,最好的事情发生在不放弃的人身上)。
这次病情的突变发生在你从中国回美国之后,我想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不能断定是因为回国延误了你的病情。你还记得吗,国内大夫在看你2013年12月3号的片子时,发现你的左前额已出现病灶,当时还小。当时你在美国没有进入新药组,回国实施生物免疫治疗是积极的态度。虽然现在看来,它的疗效没有病情发展的快。但回国3个月期间你与亲人一起生活是你人生中不会多次重复、不可替代的幸福。
在治疗方面,国内天坛医院的医生认可美国医生的放疗措施。我想,在放疗之后,如果在美国有机会进入新药组,有利于对病情的控制。此外,是否可逐步尝试加大服用贺用和大夫中药的药量,提升白细胞和加强身体的免疫力。在加强治疗方面,心情非常重要。要有强烈的生存欲望。要有尚未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感,有继续陪伴Bob的使命感。
回忆我们这一生,非常不容易。文革使我们学业中断,以后靠自己的努力追上时代的步伐。尤其你,身处异国,一个人打拼,成绩优秀。至今,我们人生中的青少年、中年阶段都已过去。在即将进入老年之际,突遇重大疾病,留给我们的一个遗憾是不能对父母尽孝。我母亲去年去世。回想往事,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妈在我家住了2个春节。在此期间,我帮我妈洗澡,陪她下棋打牌,使她很快乐。尽管她也曾发火说我们的饭做的太硬。妈妈不在时,我们多么想留住有妈妈的幸福。现在不是我们想吃妈妈做的饭,而是想让妈妈吃到我们做的饭。你的人生成绩给你的父母带来欣慰和快乐,他们为你骄傲。但这真的不够。还要再加上你为父母端水做饭,陪伴在父母身边,听老人的唠叨,陪父母聊天,这才是完整的尽孝。目前,你的父母还在,你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也是你不能随意放弃治疗的动力。还有Bob,你们相亲相爱、相互陪伴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也许你行动已不灵活,但你的存在就是他感情的依赖,是他人生努力的源泉。一定要争取再陪他多走一段时间。
在治疗方面,注重饮食,调整以往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近年国人开始注意养生,开始注意每天摄入食物的营养。我想这也是世界关注身体健康的潮流。不要小窥这些。我现在也在改变饮食,从每天的小事做起。
面对疾病的急剧进展,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也十分重要。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家中。生活起居要有人照顾。要保证每日饮食的健康。要定制每周的3餐食谱。每天要有少量的体力活动。要听听音乐。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一定有道理。只是过去我们年少时缺少音乐熏陶,后来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欣赏它。音乐的波澜壮阔,它的大气,它的优雅,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各自的史诗。经历丰富而沧桑的人才能听懂音乐。此外,欣赏自然季节中风景的变化也让人很有感悟。
你是否也可建议Bob暂停工作,陪伴在你的身边。除了陪你治疗之外,陪伴你的日常生活,陪你外出观光,给你阅读书籍,帮你撰写自传,等等。
面对疾病的急剧发展,你要像过去2年那样,冷静处置。要先安排眼前的事物,要重新规划家中的财务。将预计未来20-30年的养老支出提前使用。例如,家里要雇工,外出旅游,了结几个重要的心愿,等等。目前,如果你还没有立遗嘱的话,要有遗嘱表达对自己个人财产支配的意愿。在中国的法律中,因为你没有子女,你的伴侣、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你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我想这些年你和佐英同在美国,你们之间一直在相互帮助。你不在以后,你将个人的一部分财产(不含Bob的)遗赠给佐英一定会使你觉得欣慰。在这方面,我和新生早几年就写下遗嘱,生怕突发疾病和出现交通事故来不及做真实意愿的表达。我们的遗嘱中强调了对直系亲属的单向遗赠和对尚存伴侣再婚财产使用的约束。另外,如果你能给你父母留些钱,不论多少,是你心意的表达。这些钱的使用也是你孝心的延续。以上是我个人建议。不代表许家家人意见。
人在重大疾病面前经常经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医问药,依靠医生。当医生没有太多办法的时候,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病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要活着"信念的支撑,靠自己的生活调理,同时配合治疗。我们的一生遵循着这样一句谚语,当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就改变自己;当不能改变自己的时候,努力交给自己,结果交给上帝。
许红,不多说了,在重大疾病面前,你已经很坚强,做的很棒。我也要像你一样。或早或晚,我们都将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但我相信,我们有灵魂。我们的灵魂漂游在空中,会看到这个世界越变越好。
娃利,2014.4.26
J
Jiang,wali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February 5, 2015
许红:
你好。从你父母那得知你4月16号开始放疗。目前你的放疗已进行了1个多星期,身体的反应强烈吗?
你4月16日寄到北京的片子,于4月23日问诊时听取了天坛医院孙彦辉大夫意见。孙大夫一改往常乐观的态度,认为片子显示了多点播散,近期病情进展加快。他认同目前实施第二次放疗,提示注意观察病情。他提及对于母胶质瘤而言,发现后生存的中位期是14个月。并提示注意前额病灶的症状,不宜一个人独处家中,需要有人看护,注意癫痫病的出现。普华医院的韩小弟大夫的门诊还未约上。4月23日他做了一天的手术。目前在争取5月4-6日能听听韩大夫的意见。
许红,你近期的病情加速进展,现实十分残酷。但需要冷静面对。一是加强治疗,一是调整情绪。面对这种高级别的肿瘤,你在手术后已经争取了有生活质量的25个月的时间。目前仍有继续争取的可能。一句英语谚语说得好: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believe. Better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are patient and the best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don't give up. (好的事情发生在相信的人身上,更好的事情发生在耐心的人身上,最好的事情发生在不放弃的人身上)。
这次病情的突变发生在你从中国回美国之后,我想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不能断定是因为回国延误了你的病情。你还记得吗,国内大夫在看你2013年12月3号的片子时,发现你的左前额已出现病灶,当时还小。当时你在美国没有进入新药组,回国实施生物免疫治疗是积极的态度。虽然现在看来,它的疗效没有病情发展的快。但回国3个月期间你与亲人一起生活是你人生中不会多次重复、不可替代的幸福。
在治疗方面,国内天坛医院的医生认可美国医生的放疗措施。我想,在放疗之后,如果在美国有机会进入新药组,有利于对病情的控制。此外,是否可逐步尝试加大服用贺用和大夫中药的药量,提升白细胞和加强身体的免疫力。在加强治疗方面,心情非常重要。要有强烈的生存欲望。要有尚未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感,有继续陪伴Bob的使命感。
回忆我们这一生,非常不容易。文革使我们学业中断,以后靠自己的努力追上时代的步伐。尤其你,身处异国,一个人打拼,成绩优秀。至今,我们人生中的青少年、中年阶段都已过去。在即将进入老年之际,突遇重大疾病,留给我们的一个遗憾是不能对父母尽孝。我母亲去年去世。回想往事,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妈在我家住了2个春节。在此期间,我帮我妈洗澡,陪她下棋打牌,使她很快乐。尽管她也曾发火说我们的饭做的太硬。妈妈不在时,我们多么想留住有妈妈的幸福。现在不是我们想吃妈妈做的饭,而是想让妈妈吃到我们做的饭。你的人生成绩给你的父母带来欣慰和快乐,他们为你骄傲。但这真的不够。还要再加上你为父母端水做饭,陪伴在父母身边,听老人的唠叨,陪父母聊天,这才是完整的尽孝。目前,你的父母还在,你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也是你不能随意放弃治疗的动力。还有Bob,你们相亲相爱、相互陪伴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也许你行动已不灵活,但你的存在就是他感情的依赖,是他人生努力的源泉。一定要争取再陪他多走一段时间。
在治疗方面,注重饮食,调整以往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近年国人开始注意养生,开始注意每天摄入食物的营养。我想这也是世界关注身体健康的潮流。不要小窥这些。我现在也在改变饮食,从每天的小事做起。
面对疾病的急剧进展,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也十分重要。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家中。生活起居要有人照顾。要保证每日饮食的健康。要定制每周的3餐食谱。每天要有少量的体力活动。要听听音乐。有那么多人喜欢音乐,一定有道理。只是过去我们年少时缺少音乐熏陶,后来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欣赏它。音乐的波澜壮阔,它的大气,它的优雅,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各自的史诗。经历丰富而沧桑的人才能听懂音乐。此外,欣赏自然季节中风景的变化也让人很有感悟。
你是否也可建议Bob暂停工作,陪伴在你的身边。除了陪你治疗之外,陪伴你的日常生活,陪你外出观光,给你阅读书籍,帮你撰写自传,等等。
面对疾病的急剧发展,你要像过去2年那样,冷静处置。要先安排眼前的事物,要重新规划家中的财务。将预计未来20-30年的养老支出提前使用。例如,家里要雇工,外出旅游,了结几个重要的心愿,等等。目前,如果你还没有立遗嘱的话,要有遗嘱表达对自己个人财产支配的意愿。在中国的法律中,因为你没有子女,你的伴侣、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你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我想这些年你和佐英同在美国,你们之间一直在相互帮助。你不在以后,你将个人的一部分财产(不含Bob的)遗赠给佐英一定会使你觉得欣慰。在这方面,我和新生早几年就写下遗嘱,生怕突发疾病和出现交通事故来不及做真实意愿的表达。我们的遗嘱中强调了对直系亲属的单向遗赠和对尚存伴侣再婚财产使用的约束。另外,如果你能给你父母留些钱,不论多少,是你心意的表达。这些钱的使用也是你孝心的延续。以上是我个人建议。不代表许家家人意见。
人在重大疾病面前经常经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医问药,依靠医生。当医生没有太多办法的时候,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病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要活着"信念的支撑,靠自己的生活调理,同时配合治疗。我们的一生遵循着这样一句谚语,当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就改变自己;当不能改变自己的时候,努力交给自己,结果交给上帝。
许红,不多说了,在重大疾病面前,你已经很坚强,做的很棒。我也要像你一样。或早或晚,我们都将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但我相信,我们有灵魂。我们的灵魂漂游在空中,会看到这个世界越变越好。
娃利,2014.4.26
s
songsun posted a condolence
Saturday, December 13, 2014
最近去北京八中老三届网站,获悉许红去世。心情很压抑。网站刊登了白梅与许红在内蒙古插队的长篇报道以及许红几次回国与同班同学聚会的照片。很遗憾我在国外未能参加同学聚会或回国的时间与许红失之毫厘。
网站: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ea270102uxjd.html
北京八中原来是男生学校。1965年为了响应早出人才,北京八中成为全国唯一的十年一贯制的学校即承接北京实验二校和育才学校(小学五年制)直接入学,中学五年制。另外1965年北京八中对外招生仅90名学生(其中女生15名)。15名女生在我们班里。
现在仅有的回忆就是入学时许红坐在我的后面,眼睛亮亮的,很精神。1968年许红和穆欣欣去了内蒙插队。1969年我去了陕北插队,当年我们班潘小平的父辈与许红的父辈有交往,多少知道一些许红的情况。
我们班里十余人先后出国,许红在学术方面领先。还有我们班里陈子明1989年入狱13年,成为世界著名人物(陈子明于今年10月21日去世)
在这里向许红的家属和亲属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和怀念!
同时感谢白梅长篇介绍许红插队的经历以及Jessica Chen 的连载(如同报告文学体裁)
J
Jessica Y Chen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October 30, 2014
二次放疗后的日子
罗伯特告诉我们第二次放疗后,每个星期带许红去医院注射Avastin(阿瓦斯丁)。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其副作用极大。我想也许有一天她的药物停止了,其副作用带来的痛苦就会消失,她的体力就会有所恢复。我没意识到许红已病入膏肓,只告诉罗伯特上班前尽管把许红往我这放就行了。罗伯特说许红越来越没力气了,她很快就来不了了。
没想到开头提到的5月19日是许红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5/30傍晚6点,应罗伯特的请求,我丈夫与我来到他们家。我们将做许红在三份文件上签名的见证人。她看上去精神上还可以,但体力更虚弱。罗伯特说她已多日呆在楼上没下楼了。似乎要让她签一份投降书似的,许红显得不太情愿。拖了好一阵子才下笔。
她的签字显得有点歪扭,也无法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整个签字过程在她自己那张活动的病床边,在他们宽敞的主卧室里进行的。
到6月4日下午,再次看到许红时,她连自己翻身都困难了。后来我问罗伯特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注射阿瓦斯丁,他说已经停止了,因为许红没有力气下楼到医院去了。我意识到停止注射阿瓦斯丁也没能让许红恢复体力。突然我心里为许红不能如愿拒绝第二次放疗涌起了几分悲哀。没有第二次放疗,兴许可以走得轻松些。6月15日,我看到的许红已是极度虚弱。6月22日星期天,我和我先生去看许红。她喉咙疼,连咽一口白水也极为困难。但她还会有意识伸手去握握那天请来照顾她的女工的手臂,表示感谢。
在一日不如一日的情形下,许红越来越显得平静。我问她你有在向上帝祷告吗?她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她对任何人都没话了。我想她只在心里与上帝说话。
在最后的日子里,许红只是俩眼不眨地望着来客,眼神是空的。我以为大概是她不认得人了。后来碰到把她带进教堂的她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提起同样的情形。她认为那时许红已经不在了。我觉得她说的在理。许红的灵魂已经离开她的躯体了,也许正受到天使的接待。
7/1/2014 晚,接到罗伯特的电话,说许红于下午4点多离开人世了。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这也太快了。所以还是震惊得声音有点变了。第二次放疗就是为了延长生命,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这才一个半月啊。而且这一个半月尽是放疗后副作用的极端痛苦。
我和我先生来到罗伯特和许红家。上楼来到主卧室。许红独自躺在可控制的病床上。就像睡着似的,只是嘴唇苍白没有血色。静静地,也是两年多来第一次没有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等待着来自殡仪馆的人将她永远地抬出她们只有三年多的新家。她还没看到她们这个新居住区最后完工就永远地离开这个家了。她对生命的渴望,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对可行治疗方案的无限努力最终还是没能让她留下来。
从殡仪馆来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将许红抬下楼,在门口前作了片刻逗留。女士将一件覆盖物盖在许红身上,并问罗伯特要裸露他妻子的脸还是要将脸盖上。也许,他在楼上已与妻子做了告别,所以此时他只是目送许红被抬出正门,永远离去。在沙发坐下后,他说他们86年就认识,他会思念她的。她除了是他的妻子外,她还是他最好的朋友。
看着她是躺着被抬出这道门的,突然感到这房子很空很空,它的女主人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多少次,她就站在这门后开门让我们进来,每次都知道这动作还会重复。所以我也想不起来,上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它竟成了最后一次。
但回首以往的足迹,从下乡内蒙古,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她这一生也已可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除了没能享受退休外,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了。丧礼定在7月7日星期一。7月5日下午,我们决定和罗伯特一起去看电影AMERICA(美国)。可以让脑子暂时离开伤心事。他开着许红的BMW(宝马)来。坐上车,我无法忽略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以往每次都是两个男人坐在前面,我和许红坐在后面。偶尔拿他们开上几句玩笑,显示我们两位女士的大方,不计较他们生活中缺乏丈夫风范。今天,我无法不想这空位上曾经坐着的大活人已不复存在了。曾经的记忆从这开始也将慢慢远去。
7月7日丧礼后,灵车带走了许红的棺柩。她的遗体会被送到波斯顿与罗伯特的家人葬在一起。
安息吧,许红!每当我们走进那植物花园,看到那些椅子,就会想起你对罗伯特说的话,或,开的玩笑。
全文完。
End of English Version.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October 16, 2014
最后的抉择
我曾问过许红和罗伯特她要在中国呆多久,他们两人都吃不准这个时间。我再接到她的电话时是03/14/2014,她说从中国回来一个星期了。当时我也没意识到她刚过了生日不久,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想过这也许是她最后的生日。她向我要我哥哥的电话号码,说是也许她弄错了号码。听声音她正常如以往。我想她在中国这几个月就算没治好,至少也没进一步恶化。
但她说她一回来医生就说她的情况非常不好,必须马上做放疗。这是许红最最不愿听到的,也最最不能接受的。她说中国医生没建议她的情况有这么糟。于是她要找陈先生聊。看她如此不愿做放疗,陈先生建议她可以去听三个不同医生的意见。于是,这位要强的女士开始了她为拒绝第二次放疗的最后抗争。
罗伯特陪着妻子到波士顿等地去见了医生。如果说以往的生活里许红曾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过罗伯特接受自己的主张,包括去中国接受生物刀治疗,那从现在开始,她将发现他越来越拒绝接受。而当三位医生的意见都一致认为她的病况很不乐观时,罗伯特站到医生的立场上去了。
03/30/2014星期天,我接到许红弟弟Jeff的电话,说许红的情绪很不好,问我们是否能像上次一样,过去一起陪她聊聊。我们有接近六个月没有见过许红了,上一次就是Jeff提到的上次。那是10/06/2013星期天,我们带着祝愿她早日康复的气球到许红家与Jeff夫妇一起给许红开个小派对。
记得当时许红在木板阳台上用一个插电的小炸锅在炸裹了面粉的鱼肉。嘴里嘟囔着:"我这样做的鱼,罗伯特很喜欢吃啊。"那天罗伯特有事,没在家。应Jeff太太的建议,我们把餐桌餐椅搬到阳台上就餐。一个气球在风吹中爆炸了,像是放了一个鞭炮,些少地添加了一丁点气氛。许红还是发言的主角之一。
可今天许红几乎一言不发。她很认真地听着我先生说话。他就像平时一样说话,没把许红当病人。看到她对我先生的话有反应,我说:"不错嘛,你还听懂他在说什么。"
"嗯,听得很辛苦。"她说。
显然,她用此在衡量自己的脑子是否跟得上。她也意识到自己开始感到吃力了。而我此时还不知道医生说她只剩两个月了。这是她情绪低落的根本原因。
傍晚,Jeff有事先走了。罗伯特也忙完了他的事。于是我们一起到一间我们常去的餐馆吃饭。整个吃饭期间,我没发现许红有什么异样的表现。然而吃完饭后往外走时,许红没像往常那样左拐出正门,而是径直走向通往酒吧的门。罗伯特说:"亲爱的,门在那边。"
许红脸略带微笑,缓缓地转过身来。就在那一霎那,我意识到许红并不是像她努力要表现的那样"别来无恙"。
三天后,我先生去接许红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因罗伯特要晚点回家。这次我们都感觉到许红不一样了。但因为我还不知医生给了许红两个月的存活期,所以没有理会到许红会加速恶化。而我相信她之所以不告诉我们医生给她开出两个月的时间,是因为她不希望周围的人停止向她伸出援手。她还要为避免做第二次放疗做最后的努力。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这就是许红。
04/10下午快6点,罗伯特打来电话问许红是否在我们这。他说许红与她的车子及电脑均不在,以往她到哪去会告诉他的。他已打了电话给几个人,都没找到她。罗伯特说只能等她打电话回家了。
约半个或一个小时后,我给罗伯特打电话。他说许红还没电话回来。这下他真急了,说许红的情况很不好,医生断定如果不马上做放疗的话,只有两个月可活了。她脑子已经不太清醒了,她不能为自己做决定了。我忽然明白了前段日子许红的低落情绪从哪来。
显然许红还不想做放疗。罗伯特担心这次事件与许红要逃避第二次放疗有关。因为以前如果许红开车出去出了什么事,总会打电话联系的。有一次,许红在医院停车场轻撞了另外一辆车,她打了个电话给罗伯特问怎么办。罗伯特告诉她留个电话号码在被撞的车子上,让车子主人给她打电话。所以,罗伯特深知许红做事有始有终。这一次十有八九是出了什么事了。
傍晚8点,罗伯特来电话,说知道许红在哪了。于是我们开车把罗伯特带到一个大购物商场,这样他可以把许红的车开回来。只见两辆救护车也刚到。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许红在屋内和救护人员说话。脸带笑容,保持一副很好的状态。她隔着玻璃窗瞧见了我们,还跟我们招了招手。当时没有脑子不清醒的表现。牵着妻子的手走出来,罗伯特先前的急躁不见了,整个人淡定了下来。
对她这次好几小时的失踪,我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我给许红打了个电话问她是否OK。她说昨日她去邮局,碰上邮局在装修。她被指引到了另一个邮局,但不是平日常走的路,所以办完事出来后就开迷路了… 她说她不会再开车出去了,因为车钥匙被罗伯特拿走了。
据说许红还在努力争取获得有关数据来说服丈夫接受自己的主张,虽然罗伯特已经完全站在医生那边了。许红的永不放弃的精神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精神不是与许红的智力共存亡,而是与她的躯体共存亡。
04/14星期一,罗伯特需要回公司一趟,但不想把许红独自一人留在家。我和我先生过去陪她到5点。只见她瘫坐在沙发上,无限沮丧。见到我们,她说:
"医生说我只剩两个月。现在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我感觉还和一个月前一样。"
这大概是她不情愿做第二次放疗的最后一个表态了。而她一直都很清楚,自从病以来,每一步她都需要罗伯特的支持。此时,她知道她再也无法说服他了。"三个医生都是同样的结论… 算了,让他去做主吧… 是恶化了,到前脑了… 所有一切都让他去处理吧… "
第二次放疗对她来说就相等于死亡。她的话宣布了她接受做第二次放疗,也接受死亡。
电话响了,许红拿起手机听。不对,电话还在响。她站起身来,走向客厅的另一端。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步履老态龙钟,与4天前相差甚远。只听见许红"哈喽"了几声,而电话声却继续在响。许红才意识到,还不对,于是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另一个房间。
对于她这么快变得这么迟钝我感到诧异。没搞懂是她的病迅速恶化,还是精神上的压力和绝望导致的… 也许… 两者都有?
罗伯特回来了,我们起身告别。我告诉他们这周末我要飞到我哥哥那去看望我父母,为期三周。那是好几个月前就买好的机票。罗伯特告诉许红医生打了个电话给他,说放疗推迟几天做。并对她说:"我会照顾你的。"
许红望着罗伯特轻声地说了句:"谢谢"。
然后他们俩都让我向我哥哥传达他们的谢意。
走出他们家,我想象第二次放疗后,许红还能继续生存相当一段时间。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October 9, 2014
向上帝祈祷
自从MRI上出现了3个黑点,医生对MRI的解读不仅左右着许红希望与绝望的波动情绪,也促使许红产生了要自己主动寻找别的可能方案并说服她的医生接受的想法。委屈,绝望,痛苦,无奈,不服,抗争,渴望,抉择… 这些都需要有更大的力量来面对和承受,她开始转向上帝祈祷。不仅仅是祈祷上帝给她勇气和力量面对这些困难,不仅仅是祈祷上帝帮她跨过这个槛,也祈祷上帝能引导她平静地面对死亡,如果那终将是不可避免的。鉴于胶质瘤的存活率很低,加之这一年多来的了解,许红已经知道了她所能知道的有关胶质瘤的一切,所以MRI新黑点的出现无疑使她觉得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自己的上空。那是一种别人无法理解,自己无字形容的感受与压力。
我再见到她是6月30日,在我们家。显然MRI虽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许红已经觉得目前这个治疗方案不再 奏效了。也许她知道照这个方案走下去,就得做第二次放疗,因此许红表示了她宁愿以正常的脑智力少活些日子,也不愿变成傻子多活些年。我当时看到了她身上充满了这种坚定。同时也说明了许红已经非常清楚第二次放疗会给她带来的严重后果,延长生命的代价大得许红不愿意做这样的交易。
7月4日,许红与我们一起乘地铁去华盛顿首府看美国国庆游行。 也许是太累了,或别的原因,游行还没完,她就往回走。我们也跟着她撤。我相信她满脑子应该是塞满了她的病的事情。一个年过花甲经历了人生的人,身患绝症,我相信任何别的人都无法让她开心。这种情形下送她一座金屋,她也高兴不起来。此时此刻的的确确是考验她驾驭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够的时候,只能向上帝祷告,别无它法。
7月7日,许红在我们家共进晚餐时,谈的是一些别的治疗方案的可能选择,并很想搞清楚某种药的性能,包括它的毒性,副作用等等。显然要避开像第二次放疗这种会严重伤害脑功能的选择。我想医生不会花时间去回答她所有的问题,陪她探讨。我相信此时若有个对癌方面的药物有所知的人肯花时间与她聊聊,她会高兴的。于是我让她与我哥哥在电话上聊。一个小时左右聊下来,许红显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兴,说绝对还要打电话给陈博士。于是跟我要了他的电话号码,说自己不会客气的,然后满意地回家了。
7月19日那天,许红给我打了个电话,情绪极为低落,说昨日MRI的结果不好。对于来自她体内强大的敌人,我们谁都没辙,只能用形式表示安慰。第二天,他们的朋友大卫也过来我们五人到餐馆吃饭。第三天,我先生和我带上许红到外面随便走走。由于她本就不好运动,此时的体力和心情会更显不足。我们不久也就打道回府。
许红提起陈博士宽慰她要保持心情愉快,做些诸如静坐,打打太极拳之类的东西。我说我可以和她一起练太极拳。她说那将来到我家来跟我一起打太极拳。我说行。她说有人告诉她,我们这附近有些华人区域有老人活动。于是我们也一起试图去寻找过。我觉得她开始在考虑办理退休,又很担心退休后在家无聊。不过我心里清楚,只要MRI结果不再令人悲观,她马上就会打消退休的念头。不管她对工作喜欢与否,工作已经成了她生活中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当我学会简化的二十四式太极拳时,她已经不再提太极拳的事了。不过我自己倒受益了。虽然只花5分钟打一次24试太极拳,但只要每个动作都到位了,每天五分钟还是能感觉到受益不浅。特别是走路的脚步也觉得轻巧多了。但我看许红还是买了些太极拳和瑜伽的录像带。也许她想将来再学。毕竟这是炼身防病而不是治病的东西。对她而言,目前只有一门心思, 就是治病。她使用了做教授的本事,广搜有关可以治病的信息。逐渐地她把目光锁在一些临床试验上,希望在这些临床试验项目中,能找到一个和自己的状况对得上号的。
我想这即符合她的性格,也让她能以一种有"目标"的方式来度过这段绝望的日子。加之有陈博士陪她探讨,诚心地给她安慰,那是这段艰难日子里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了。用她自己的话推译就是上帝应了她的祈祷,借用别人的手,给予她帮助。此后,她多次向我表示:"你哥哥人真好。"
66年文革开始,中学关门,大学也关门了。从68年下乡到内蒙古起,,她就不停地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能走到今天,她坚信是永不停止地争取和创造机会的结果,这种信念一直没有消失。也许如今她面对的是一条死胡同,但那种不断尝试的精神还活着。这种精神与她的躯体共存亡。
在那些临床试验项目中摸索一阵子后,许红发现没有她符合条件进入的。到此为止她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8月12日2013年在我家时,她向我们宣布了她要回中国试一把。她把目光锁定在脑胶质瘤生物刀这个项目上。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听起来更让人激动。因为它是通过调节和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来消灭肿瘤细胞的。显然用这种方式消灭肿瘤细胞会来得更彻底。她非常渴望能在美国做生物刀治疗,因为她相信这里的技术会更好。但也许是由于美国严谨的态度以及极高的要求,美国目前还没有接纳患者进行脑胶质瘤生物刀的治疗,或临床试验。
她认为中国方面技术恐怕也并不成熟,但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是最后一个合理的机会。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那也是一个希望。甚至这也可以是许红逃避这里的医生要她做第二次放疗的很好理由。不管怎样,也无论将来成功与否,我想从许红的心理来说,这是她必须走的一步。至少到了弥留之际她没有什么可撼的,她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自己可能做的一切,尽了自己所能尽的最大努力。
但要到真正可动身前往中国治疗,这期间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她没告诉我其中的细节。但我知道她要到中国去试一把生物刀的决心坚不可摧。10月18日我接到她的一个电话,她情绪极为低落。但没提及具体的什么细节。这是她动身前往中国前我们之间最后一个电话。
她说她要回一趟滨州家里及学校。并说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回去了。 这次回去,她还要到教堂去接受洗礼,昄依基督。罗伯特和许红弟弟开车陪同她前往。感恩节前后,我听说她已要动身前往中国,想必准备工作已一切就绪。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Friday, October 3, 2014
再次心碎
暑假后,许红回滨州上班。能再重返岗位就一直是她的心愿。想到要整日呆在家里让她觉得痛苦,六十年风雨人生还没来得及为今天培养业余爱好。所以她绝不会辞职卖掉滨州房子回维州家养病。现在病情的稳定使得她能重拾往日生活,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她高兴的。好像是刚经历了一场龙卷风,龙卷风过后风平浪静。
我们都各自忙乎自己的生活。日子在悄然中又滑过了半年,迎来了另一个圣诞节。我先生去了许红和罗伯特家参加圣诞聚会。这半年来,我们没有听到关于许红MRI的坏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此,不仅我没认为1月1日2013年会是她最后一个新年,我还认为她会有更多新年在前头等着她。
1月1日2013年傍晚,许红,罗伯特,我们和许红弟弟夫妇在餐馆会餐度过新年。虽说心里还装着许红身患癌症一事,但完全没了'此人会很快就离我们而去'的想法。只感觉就像她曾表示过的,再干几年就退休了。我琢磨她大概想在65岁退休。只有4年2个月之遥。看如今状况良好,我心里毫无疑问她能走到那一天。新年过后,我们又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每几个星期许红就会做一次MRI。二月九日,我们四人在餐馆一起吃饭。没听说到什么乐观的消息,也没有什么沮丧的消息。我觉得能保持这样的现状也不错,相信别人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吧,包括许红。我想以下的十年,至少五年都会是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去年这段日子,许红被诊断患了脑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今天已经打破了医生'一年存活率'的预言。
看上去,许红此时的心情比较平静。她与罗伯特还谈起用ph检测纸去测试身体的酸碱度。以便控制身体不要滑入酸性体质状态。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她主动谈论保养身体的话题。去年患病后,对于弟弟出于亲情心理而抛给她的一些养生说教,许红表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也许,此时的许红对战胜疾病有了信心,对新生命有了希望。于是对生活事项中的优先次序进行了调整。曾经在生活中被忽略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一场病后突显了它的重要性。
患胶质瘤一年后的许红还没失去她享受生活的能力,确实是可喜的。我想一切都在恢复之中。这是人生中的一次不幸,但作为幸存者,她是不幸中之万幸。一种能逃避被胶质瘤置于死地的饶幸心理不仅存在于我的意识中,也在许红的心中发芽。
风平浪静的日子继续延续到五月的一天,被一声巨雷打破了。许红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说MRI出现了3个黑点。我吃惊地脱口而出:"什么?"引出她哽咽的喉声,但马上她控制住了自己。也许是安慰她自己也是安慰我,她说还不确定这些黑点是癌扩散还是细胞坏死。我心中刚被扑灭的希望火焰又重新燃起。我本能地挑了我想听的部分,认定那是细胞坏死。
我感觉到这不幸的消息对她的震撼极大。我让她当晚到我们家吃饭。正值那晚她的罗伯特不在家,我叫我先生下班后把她接过来。见到她我无语,我找不到可以安慰她的话。而脸上,她已经恢复了她往日的平静。只听到她沮丧地说了声:"我以为我已经跨过这个槛了。"
她有理由担心,因为她说她的左眼察觉不到眼角内的物体。她示范着把她的两个手臂向侧面平伸出去。她的右眼角可以察觉到右手臂,但左眼却感觉不到左手臂的存在。那时正值我的左眼出现黑点,眼角视力稍有模糊。我提出这一点想解除她的担心,即说明未必与癌有关。但她显然不接受。打她病以来,她就一直在电网上搜寻与其有关的信息。对于视力与脑癌之间的关系,她恐怕已经心里有数。
对于她我的心理就是希望出现奇迹。而力所能及的就是罗伯特出差的时候我叫她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不觉得这对她的心理感受能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但看她喜欢与我先生聊天,我想总比自己一人在家好吧。想搞清楚目前的治疗方案是否还有效,想了解是否有其它可行的方案,这种迫切的心情都写在她脸上。她也将把作为教授的做科研本领都用在这上面。
而且,她还坚持说她能自己开车到我家,不用我们去接她。虽说只有约4英里,但需要拐弯的地方还真不算少。由于有意识自己的左眼角看不见东西了,她向左看时,会把整个脑袋都转过去。我希望在以下的十年里她都能继续自己开车到我家。
此时等待下一个MRI的心情一定是一种煎熬。在我看来,对她而言那简直是生与死的宣判;在我看来,这比曹丕命令曹植在七步内做完诗,否则就没命还要残酷。因为曹植施展了才华,就能救自己一命。而许红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施展。MRI 的好与坏对许红来说就是希望与绝望的代名词。希望与绝望的不断交替,会让人心衰力竭。渐渐地,她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撑不起这般折磨。她需要一只强有力的臂膀搀扶着她前行。
和她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年轻时许红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随着毛死国门打开经济改革,毛从神坛上掉下来回到人形。信仰破灭了,大多数人也就没再试图去信仰什么。此时突然面对好不容易然起的那点希望之光就要熄灭,我相信她一定要崩溃了。终于,刚走过六十岁的她,觉得自己需要新的信仰。需要吸取新的力量来面对这些她作为一个俗人无法面对的绝境与苦痛。
我想起恰是一年前,去阿拉斯加的前一个月,即5月份,我们和许红夫妇四人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植物花园去。95英亩的植物花园坐落在小丘陵地带上,给人一种层次美和立体美的享受。园内保留了大量的树林。幽静的小径边上,设有许多人们为纪念已故亲人而捐献的椅子。当时许红对罗伯特说:"我死后,你给我在这弄张椅子。你和你的女朋友或新太太有时可以到这来坐坐。"那时正值许红的状况日渐好转,我权当那是玩笑。
不料正好一年后MRI就出现新状况。这使我回想起在那之前,即3 月份,许红带我们俩到那植物花园去过。那时她在做放疗,因吃了配合放疗的药而脸部浮肿。但她却很主动地要求三人一起照了几张合影,还轻声地说了句也许最后一次在一起了。那时看着那些纪念亲人的椅子,她就说要叫罗伯特给她弄张椅子。因那时的她状况不算好,听起来有点伤感。回想起来,那次她好像在跟我们告别。她也许渴望比她年轻得多的丈夫不要把她给忘了。毕竟墓地远在波士顿,那是早几年买好的,和罗伯特的家人一起。但若在家附近有张纪念她的椅子,她共处了二十几年的丈夫就可以去看看她。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当时她对罗伯特说这话时,不是100%在开玩笑。至于我本人没想明白的是,她不太想把照片给我们,说明合影并不是为了要我们记住她。而她若要离开人世,为何要留下和我们一起的合影?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September 25, 2014
阿拉斯加游轮之旅
六月中旬转眼就到了。对于许红来说,起码几个月来难于言状的懊恼苦痛到此告一段落。MRI的可喜结果及现代越来越好的治疗技术悄然地在她的心里滋养了一丝能跨过这个槛的希望。而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则认为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以后的人生就是吃药控制就行了,就像我父亲半个世纪来吃药控制他的高血压一样。
于是,六月十五日,我们一行四人登上了早晨八点多钟的班机,从华盛顿首府飞往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到了机场,我们找到了比我们先到的罗伯特的八十几岁的妈妈。然后坐上我们预先订好的车直奔我们要乘的客轮。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排队上船,但我心里想的是去哪里弄点吃的。飞机上吃的那点东西已经消化完了,此时好饿。
我被告知一上船就有东西吃。于是我的注意力就全在登船上面了,渴望快点爬上那高高的客轮。我原以为船上要到了吃饭的时间才会有东西吃,没想到上了船的第一惊喜就是有一个自助餐厅二十四小时提供食物。我最喜欢就是旅游能带上餐厅这一点。餐厅的入口处还放了免水洗手液,使人觉得几千人的轮船上消毒卫生工作做得很到位,让人放心。
几餐饭后,让人觉得在轮船上吃饭可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不仅品样多,还同时有西餐和亚洲餐的口味,而且味道还很可口。我不是个很喜欢甜点糕点的人,可船上的甜点糕点却如此好吃,以致于我天天都吃。难怪旅游结束后我们被要求填一份调查表,在问到旅游的目的是什么时,其中给出的一个选择答案就是"船上的食物"。十四天吃下来,我能明白也理解有人就冲食物而来的,特别是老人,上岸游玩体力有限。正如罗伯特的妈妈,这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享受游轮之旅了,包括有人给她洗衣服,因为她是多年的老顾客。这次回去后,她的体力就明显下降了。最终还是离开居住多年充满回忆的家,住进老人公寓。
许红以前不只一次坐过轮船去欧洲旅游,所以她已经知道食物好吃。但此次的悲哀是她无法品尝到美味了。而我总想有一天她不需吃那么多药的时候,她的嗅觉会恢复的。而此时相对于癌本身来讲,能控制住它才是大事,嗅觉就显得是件小事了。至于感受上,她把这次游轮之旅看作是人生最后一次旅游,还是由于MRI没有负面的结果,她也就没这么想,我就不得而知了。
爬上船的顶层,看到用网罩住的蓝球场,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忍不住抓起篮球投了几个蓝。还要先生替我拍下几张照片。这时才反应过来,难怪刚才在餐厅吃饭时,天花板上传来什么东西敲打的震动声。突然我意识到这客轮不只是把旅客从A点带到B点,以及提供食物而已。它还试图提供旅客各种娱乐和享受,以便在茫茫大海上独行时消磨时间。
船上有商店,桑拿,游泳池,图书馆,照相馆,酒吧,餐馆… 还有个赌场,但只能船在海上航行时才能开业。因为在海上就不受到任何国家的法律约束了。晚上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或到戏院看表演。感觉就像是一座漂泊在海上的城镇。难怪以前听度完假后的人说过不想回家。虽然对我而言,不管到哪,最终还是回到家的感觉最美妙。
船上配备了足够的救生艇。艇上都有编号。我们记住自己所属的号码及艇停放的位子。艇上有一定量的食物及水的储备。轮船有个万一的话,每个人都有生还的机会。
6月15日下午5点,我们乘坐的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号轮船启动了。
我们的阿拉斯加航行路线是: Seattle(西雅图) - Ketchikan(凯彻卡恩) - Tracy Arm(特雷西臂) - Juneau(朱诺) - Icy Strait Point(冰峡点) - Anchorage(安克拉治) - Homer(荷马) - Kodiak(科迪亚克) - Hubbard Glacier(哈巴德冰川) - Sitka(锡特卡) - Victoria(维多利亚) - Seattle(西雅图)
轮船缓缓地离开西雅图。和许多人一样,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远方美丽的Rainier(雷尼尔)雪山。我们四人就以这雪山为背景,倚着栏杆合影,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十四天后带着阿拉斯加美好的记忆回来时,却忘了再看一眼雷尼尔雪山是否美丽依旧。我想大概是没在甲板上的原因吧。虽然一路北上时,看了无数连绵不断的美丽雪山,但它们与这海拔四千多米的,类似日本的富士山的雷尼尔雪山有着本质和外貌的差别。
当天晚上上床睡觉时庆幸大船行驶的平稳。然而第二天还没起床,船身就大晃动起来。挣扎着撑到餐厅,渴望能安慰一下空空的胃。却经不住一阵接一阵的呕吐。连吞下去的晕船药也吐了出来。以往晕车呕吐那不堪回首的感受全回来加盟到这次晕船的感受里来了。而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厉害至少10倍。胃疼接踵而来。我明白已大伤元气。心里思忖着如果一路船都这么晃的话,我恐怕难活着回去。但我没有打道回府的打算。只是想着每熬一天,就如同一年似的漫长。6月16日,船整日在海上行驶,没有靠岸。我也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把希望全放在轮船靠岸的时刻,那是我可以缓口气以求苟延残喘的宝贵时光。
17日一大早,船终于稳下来了。这比吃什么药都灵,不晕了,除了胃疼外。早晨8点,船靠岸了。我们来到了阿拉斯加第一城市Ketchikan(凯彻卡恩)。到下午5点船再次开航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岸上活动 (shore excursions)。 每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游玩项目事先买好票。而此时最让我高兴的还是不用去找吃的。只要乘电梯上楼到自助餐厅去就有可口的东西吃。我太渴望这顿早餐了,胃空空的,好像许久没吃过饭似的。
我们与许红一家相见在餐厅。许红说以往她和罗伯特乘轮船去玩从没发生过这么厉害的晃动。罗伯特从没晕过船的,这次也受不了了。说完后她对自己没有晕船有了几分得意。许红竟然没有晕船,更使我觉得她闯过了鬼们关,癌从此成为历史。我想她身子底子好,所以她跨过了这一关。但同时又隐隐约约地扪心自问,是否这种缺乏敏感的体质使她没能收到身体发出的警告而错过了人生中注意身体保养这个环节?
吃完早餐感觉很好。出去玩没有吃饭的后顾之忧真好。玩回来就有可口的饭菜吃太好了。而更棒的是走进阿拉斯加树林里呼吸到的无比新鲜清纯的空气。此行的最高享受就是阿拉斯加的原始美。原始的水域,原始的树林,原始的空气,原始的岛屿,原始的岸边峡湾,原始的白云缠绕的连绵雪山… 那是一种真正被大自然怀抱的感觉。
每当轮船在海面上孤舟航行时,船上的赌场就开始营业。为了填补我脑子里对赌场这个概念的空白,也为了满足心里的那点好奇心,我光顾了赌场。给自己定的损失额预算:不准超过一百美元(我知道赢大的机会是零)。
我们几个拿它取乐,每一个小赢都哈哈大笑。引来周围的人凑上前来,以为我们赢大了。发现我们并没大赢,有的嘟囔一句扫兴离开。人家大概无法明白我们怎么会为那一点小赢乐成那个样子,因为那点小赢还不足弥补那输掉的。也许是因为我们走进赌场时带着的就不是一颗赌心。而是好奇,消磨时光,寻欢作乐,甚至对许红而言,暂且忘掉烦恼…
动手玩的就我和许红。我们能加倍作乐的时间,因为我们不同时玩。她玩时我看,我玩时她看。即便如此,钱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输掉了。这种乐是昂贵的。如果输过头了,取而代之的将是撕心裂肺的痛苦。
有一次,我和我先生经过赌场时,被眼前的一幕逗乐了。许红独自一人静静地,专注地坐在机器前赌玩扑克牌。她说睡不着,就独自上这来了。我想,如果这能让她一时冲淡或忘掉自己身患癌症,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许红是生在50年代中国的人,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给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就注定了她不会放任自己,因此,她会把自己的输款控制在一,二百美元之内。
毕竟赌场不是一个可以久呆之地。那是全船唯一一个可以抽烟的地方。所以那里烟味呛鼻,空气混浊。与甲板上海风送来的新鲜空气,及阿拉斯加原始生态里的超纯空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之第二星期玩赏的项目多,所以第二个星期我们就很少光顾那里了。
当然,提起阿拉斯加旅游,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川。所以,当就要接近冰川的时候,全船的人都激动起来,全涌到甲板上等候。这一程我们总共看了三个冰川。第一个冰川是我们启程的第四天,船在Tracy Arm(特雷西臂)近距离地观看了South Sawyer Glacier(南艘叶冰川)。带点"Z"型的冰川湛蓝中夹带着白和黑。大家手里那不需担心胶卷的数码相机"咔嚓""咔嚓"地忙开了。虽然我们知道颇具气势的巨大冰川还在后头,但头次看到冰川,虽小还是觉得挺饱眼福的。
启程的第五天,我们来到阿拉斯加首都Juneau(朱诺)。在这里我们看了Mendenhall Glacier (蒙登豪尔冰川)。这是我们可以用两条腿走近观看的冰川。可以看到时不时有小飞机在冰川上飞行。显然有人不满足于只是观望,于是乘飞机降落到冰上行走,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连续两天的冰川体验足够我们慢慢回味感受,等待回程时才会去看的雄伟Hubbard Glacier(哈巴德冰川)。
第八天,即22日早晨7点,我们到了城市Anchorage(安克拉治),也是我们航线的最北点。晚上11点,我们开始返航了。第11天,即25日,我们出发向期盼中的大冰川Hubbard Glacier(哈巴德冰川)进军。这大概算是把整个海航旅游推到最高潮吧。那些没有体力上甲板去融入人群中的老人,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从窗口张望。
还没看见冰川,两边云雾缠绕的,绿色植物及白雪相间的连绵山峰,以及其倒影的美丽就先把我们给迷住了。随着船缓缓地前进,在陶醉周围景色中带着看大冰川的渴望,此景此情只有亲临其境才能体会得到其中的美妙。
一块从冰川上分离下来的,颜色比别的浮冰丰富的湛蓝色带黑条的冰块漂过我们的游轮,我满意地高兴地将它纳入了我的镜头。突然,一艘小船进入我们的眼帘。没想到在这寒冷的冰世界里,我们并不孤独。小船的顶上整齐地摆放着13根钓鱼竿。如此之小舟上竟挤满了六个人。我想他们想钓的鱼一定是很有经济价值,或鱼肉鲜美无比。不然怎么会孤小舟开进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冰世界里。我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船坏了怎么办?站在冰川上的生还概率也要高于掉进这刺骨寒的冰水。我马上给自己一个说法打掉这份担忧:也许他们带着吹气的救生艇。
随着水面的浮冰越来越密,我们越来越靠近大冰川。终于,Hubbard Glacier(哈巴德冰川)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前面看过的两座冰川,与这座宽度无法全进入我的相机,十层楼高的以蓝色为背景的冰墙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时而会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一堵冰墙倒塌入水。由于那天云雾重,冰川后面的山看不清,只有若隐若现的山顶仿佛是天上仙境。这浩大的冰川,与它周围的冰山冰水及密密的浮冰一起,给人一种寒气逼人的美。这种美无法用文字表达。航行第一天那伤元气的晕船换来今天这独特的冰寒美的享受,值了。而后来,船身就没再有那样大的晃动了。
而另外两处具有的触动心灵的美是相机无法拍摄得下来的。1)在Kodiak(科迪亚克)下了游轮,我们四人决定到 Fort Abercrombie State Park (福特•艾伯克伦比国家公园)。这里的自然美远远超过了任何人工修饰的公园。如果说在Ketchikan(凯彻卡恩)当我走进原始森林时,林中的超新鲜空气感动了我的肺腑,那这里不仅有可以与那里相媲美的空气,还有我意想不到的,用笔墨和相机都无法记录下来的自然美。有崖,有水,有树,有鸟,有各种植被,那天还有一只老鹰站在崖上久久不离去,任我们拍照。我从没见过一幅风景画能给我如此之美的震撼。当我们偏离小径稍稍往深处走时,我的心被这安静自然原始的氛围溶化了。我想如果我不食人间烟火,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待会我的躯体就要离开这里,但我愿意把我的灵魂留下。而作为一个俗人,我真想把这里的空气压缩了带回家久久享用。
2)在Sitka(锡特卡)下了游轮,我们四人与另外一对夫妻合乘一艘小游艇出海。也许许多出海的人在期望看到鲸鱼,我更感兴趣的是深海处的一座座小岛。因为看鲸鱼不需来到阿拉斯加。在New Engliand(新英格兰)就可坐上观鲸船前往鲸鱼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深海处的小岛不许住人。岛上树木茂盛,原始没有污染,岛边的水清澈见底,老鹰在树梢上造窝繁殖后代。而海中光秃的石块上,是海狮们喜欢栖息的地方。每个岛都有其自己的特点。有的岛上有积雪溶化流入海的瀑布。在海风抚面的舒适下,这一幅幅移动的自然风光怎能不打动任何人的心?这是任何人工巧手打造的华丽都无可攀比的;任何相机都无法把这总体的美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但愿阿拉斯加的原始美永远不会被破坏,从而得到永生。
6月29日八点多钟我们在西雅图下了游轮,结束了为时14天的阿拉斯加游轮之旅。感觉上,这不像是许红人生中的最后旅行,反倒像是在庆祝她成为癌症幸存者。更多的旅行还在后头等着她。
许红似乎也回到她的正常生活中去了。因为下一次我们再见面是6个月后的新年。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Saturday, September 20, 2014
手术后
接下来就是化疗和放疗,希望进一步将余留的癌细胞消灭。医生家人朋友告诉她一些病人活过了医生给出的存活期。许红慢慢从绝望中走出,把那1% 的希望化作99% 的努力。
3月4日晚,我们几个人在许红家里给许红过60岁生日。有感于她在这以后还有多少生日,也以为她会从此撤职在维州的家里养病,我在给她的生日卡上写下"放慢脚步,拥抱这春里一切新的开始…",以及神会为她铺开脚下的新路,带着她走向将来更多更多的生日… 我想如果医生也回天无力,那能保佑她的也就只有神了。
至于许红, 她再度声明了她不相信她的工作与她的脑癌有任何瓜葛。也许这暗示了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回去工作的。虽说一些癌患者生存多年的例子给了许红一丝希望,然而由于瘤长在头部而不是别的位置,这使许红多了一份比生命更甚的担忧。倘若放疗真给自己的头脑带来严重的伤害,那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整个治疗期间,许红频频地检测自己的手指是否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自己的思维运作是否还正常。 那份焦躁烦恼与无助,恐怕只有她自己才深知其滋味。
有一天,她懊恼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带她到医院去找她的汽车。她到医院去看病,车停错了地方但离医院不远。她走路找到了医院,但出了医院却找不到汽车。所以她坐出租车回来了。这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正常人也犯的错误。但此时的许红处于非常敏感时期,每样事情她都与她的病挂上钩。当然,她有她担心的理由,她说这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由于平时出门都是我先生开车,我对路况并不太熟悉。在她的引路下,我们来到医院。在停车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她的宝马。她回忆她好像拐进了某个名字的街道。于是我要把街道名打入GPS定位系统。由于平时从不把GPS取下,现在急忙中更是不知如何拿下。这样输入会比较慢。突然间,许红怒不可耐伸手强行去扯GPS。我从来没见过她失控。突然感受到她把这次事件看作是病后她脑部功能衰退的迹象而无限的烦恼。然而她的担心还不止这些,她不想让罗伯特知道这事。想必她想尽快在罗伯特下班之前把车子开回家。也许,她想继续在罗伯特面前保持一种能干的状态;也许,她想这事件会削弱她说服罗伯特接受自己的某种医疗主张…
最终我们拐进一个地方她觉得挺像的。她说她记得继续往前开。突然间,她高兴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我的车吗?"手指着就停在我汽车前方的宝马。找到汽车的那份高兴劲彻底淹没了她先前那种压抑失落的样子。
人都说,平时病菌就存在于我们肌体里。当我们弱的时候,病菌就强盛起来,把我们击倒,让我们生病。生活也是如此。我们来自动物,因而与动物分享着某种特性。当动物感到威胁时,就本能地让自己显得壮大。难怪人也想显示自己的强势,担心弱了被吞食。也许,许红很清楚这一点。因而,在来自疾病本身的压力外,她还感到了来自另一个层次的压力。
在心理上我仍然很难接受她有生命威胁这个事实。直到有一天我们坐在她家聊天时,我发现她在举起左手时,手指有所颤动。她的瘤长在右脑下部。据说右脑控制左侧,左脑控制右侧。这时我才突然看到"死亡威胁"和许红的人生接轨了。心里不免一震:真的吗?一年后,坐在我面前这位看似健康的人会从此消失了?我不愿也不敢再往下想。
她需要常常光顾医院。我陪她去了几次。她看到许多癌症患者独自一人到医院接受治疗,于是,她决定要学习一种新的坚强。自己还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去完成。她发现自己还可以开车,所以大多时候就自己上医院了。能开车的本身也告诉了她,化疗还没对她的大脑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是她每天最为关注的事情。MRI也就成了她最最难面对的。可以想象她怀着怎样忐忑的心情去聆听MRI的结果的。病情的好转还是恶化就全显示在那上面了。而好转与恶化送到耳朵里就只转化为一个字:生或死。因此,要面对MRI的结果,需要预备何等的心理承受力!所以有时她也让罗伯特先听结果,然后再慢慢告诉她。
疾病促使她去了解这种病。然而,越了解越让人失望。四月份,她才开口对我说她得的是胶质瘤母细胞瘤第四期,是癌症中最致命的一种,又是晚期。放疗开始了。由于知道掉头发是化疗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和我先生陪许红去买了假发。后来,发现她除了掉点头发外,许红没有虚弱的表现。我想亏得她身体的底子好。同时也在想,她在吃的日本灵芝浓缩液是否也帮了忙?
幸运的是,一个接一个MRI下来,都没什么坏消息。我和许红都想知道,是否癌细胞不复存在了。许红说医生从来不肯用"没癌细胞了"这个表达法。这使我们觉得这好消息里有一种什么缺憾。渐渐地,许红弄明白了。那就是和别的病不一样,平时我们得个什么病被治好了,也就可以把它忘了,以后不会再得了。可一旦得了癌,以后的人生里这个字都会如影相随,它不会完全走出你的生活。你不能指望把它根除,只能求不扩散,求被控制住。于是,许红也高兴了起来。若能控制住不扩散,她也满足了。
借着此时病情与心情的稳定,许红决定乘坐游轮北上阿拉斯加旅游。她一直就想去。如果此时不去,以后病情恶化就去不了了。现在定六月份的船票,到时放疗就结束了。但为了预防万一,许红还是决定要给船票附加保险,以便随时可以取消并得到相应的退款。包括已经上了船,也可在下一个靠岸处下船返回。
许红和罗伯特邀我们俩同行。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前往。我之所以考虑再三,是因为我本来就有晕车的毛病,我知道船要比车可怕得多得多。想到晕车晕船,我就心有余悸。但考虑目前身体比年轻时好了许多,而大船相对比较稳,加之轮船沿岸而上并非驶入深海,于是我不想放过对阿拉斯加一探究竟的机会。毕竟它与美国大陆完全不同,充满了神秘感。
于是,我们一行四人,托了一点罗伯特妈妈的福(她是该轮船公司的老主顾),买了六月份船票北上阿拉斯加,为期两周。当然,我们得先飞到西雅图,从那登船。也将在那会师罗伯特妈妈,她将从波士顿飞过去。
剩下来就是期待了。
有时,罗伯特出差,我们就叫许红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聊聊天。许红说,药物已经使她无法感受得到食物的味道了。癌,首先夺走的是她对吃的享受。渐渐地,我看许红的手指不再颤抖了。我想大概她的大脑适应了她新的状况。我把它看着是个好的征兆。所以也为她高兴。加之看她的副作用并不厉害,我想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曙光就在前面。
好几年前,许红和罗伯特在许红工作的大学附近买了房子,准备退休后居住的。他们喜欢那里的环境。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对家人朋友的不舍,许红多么希望能在这世上多逗留些时光。"能再给我十年我也满足了"她说。而MRI继续呈现稳定的结果,燃起了许红心中希望的火炬,让她有个好心情,给她的阿拉斯加之旅作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September 15, 2014
手术成功
第二天傍晚,我们一直等待的电话终于来了。听起来罗伯特的声音比上次好了许多。"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好消息。接着罗伯特又告诉我们许红醒过来了,她能移动她的手臂,她还是原来那个许红。他们俩对医生的手术感到很满意。罗伯特的心情显然好了许多。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我先生提出第二天由他开车我们一起前往医院。
星期二,2月14日2012年。罗伯特,许红弟弟和我们共四人开车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 它位于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 (Baltimore)。这里最有特色的美食是螃蟹肉饼。 我们四人都暂时被笼罩在手术成功的好消息里。所以心情还比较轻松。也还有些少的聊天。只听人说过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我自己心里认定这是良性的。而手术成功,就意味着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它将成为许红漫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
一个多时后,我们的车子缓缓地开进了医院的停车楼。跟着罗伯特我们直奔许红的病房。上楼期间,我们瞥见了礼品店。这才想起我前一天光顾担心忘了预备东西。于是先进了礼品店。也许不光我一人忘了,礼品店里的人还不少。
来到病房,只见许红头上缠着纱布,坐在轮椅上。她微笑着,一边讲话一边移动她的手臂和手指。似乎在告诉我们她一切正常。她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很难想象她刚经历过一场令人提心吊胆的手术。我想她的这场浩劫就此打住了。
不一会护士进来将许红推去做MRI检查。我们四人就到楼下吃午饭去了。等我们吃完饭回来,许红也已回到病房。
中国人一般都会尽量给生病的亲人做点特别的饭菜,许红弟弟也不例外。照顾他姐姐吃他带来的午餐。
我对癌没有更深的了解。因此我安慰许红说一旦她星期五出了院,这一切就成为历史了,她还会是原来的许红。许红很高兴地说:"我就当你的话是真的。"
此时的许红心情很好。她非常高兴她能控制自己的手脚,非常高兴脑功能完好无损。这是她最担心最关注的一点。换句话说,她充满信心她还能回去工作。她的好心情传染给了罗伯特。当许红问他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导致的,罗伯特幽默了他的妻子:"医生说都是做丈夫的错,糟烂的丈夫。"
这时许红期盼的是但愿这脑癌不是从身体别的部位扩散而来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太迟了,一点希望也没有。而脑部的癌一般不会扩散到身体别的部位。
为了给他们俩人一点空间,我们三人来到等候室。后来,许红弟弟也到病房去了。我们俩没去。我想他们大概需要一点"家人"时间。我心里没有准备还会听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只盘算着离开之前到病房去跟她说声再见。然后叫我先生星期五请个假我们一起来接许红出院。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骇人听闻的消息就在我们盘算着差不多该回去的时候爆发出来了。
罗伯特带着感伤来到等候室,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回去的话可以先走。他要留下来陪许红,许红现在逾常难过。我有点不解,先前不是因为手术成功挺高兴的吗?怎么突然如此悲伤?
看我不解地望着他,罗伯特进而解释道,护士刚带来了医生的话,说许红只有一年左右的存活期。这句话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宣布她患有脑癌,因为我没把脑癌理解成即将死亡。我的心顿时像被什么东西抓了起来,很紧很紧。好一阵子呼吸没那么自如。到此为止,我与许红虽然认识很多年了,但因为她住得远,我们走的并不是很近。可即便如此,我受到的撞击还是蛮大的。那么可以推测许红应该像是听到了对自己宣读死刑判决书一样。这一惊自然是非同小可。
当然这里有个文化的差别。在中国,这种消息,一般只对病人的家属说,避免惊吓本人。自然结果也就是常常由家人来做治疗方法的选择或决定。但在美国,普遍认为,一个成年人有权也应该知道自己的病情,并由本人做决定要选择何种治疗方案。在本人有能力作决定的情况下,别人是不能擅自替他做决定的。许红毕竟是中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对这种直接了当一时感到很难接受。
我们告诉罗伯特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他。我思忖着是否该跟着罗伯特进病房。我不是她的家人,所以估计这种非常时期她或许不想见外人。所以就继续僵坐在那里没动,想象着如果我处在她现在的环境的话,什么话都安慰不了我。从这一刻起,左右她的喜和乐的就只有医生的话了。也是从这一刻起,我与她的见面将比以前频繁。并目睹了她以下两年多来的一些变化。
我原以为脑瘤成功被取出来了,就意味着病治好了。对"癌"有所接触的丈夫跟我解释说手术成功并不等于所有的癌细胞都清除干净了。只要有一个癌细胞存活,这个癌细胞就会继续扩散。原来癌细胞如此难对付,难怪人们谈癌色变。
傍晚时分,罗伯特来到等候室,告诉我们许红现在好多了,她叫我们大家先回去。于是我们来到病房向她道再见。她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我想,是他们用了什么话这么有效地安慰了她;还是许红这么快就给了自己一个说法;抑或是给她吃了镇静药?总之,没有留下一点刚经历过情绪动荡的痕迹。此时还有一个小小意外,那就是医院通知第二天星期三出院。原本以为是星期五。
我们四人离开病房时,天黑下来了。一路走到车库只听见我们自己的脚步声。谁也没说话。与来时不一样,回去时心是沉甸甸的。感觉才刚刚在一起送走旧年,迎来新年,就被告知她在这人世间只剩一个新年了,真真不是滋味。
分手时,罗伯特说他自己来接许红出院就行了。我们也不坚持。我想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能把癌细胞都杀死,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帮忙。我们都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境地。也许是我的情绪起伏比较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认识的人变成癌症患者。对于我先生来说,癌曾在他妈妈不到60岁时夺走了她的性命。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Thursday, September 11, 2014
两年多前
近十几年来,我们大部分的新年是在许红的旧房子度过的。许红,罗伯特和我先生毕业于同一个大学。2008年美国房地产业危机,房价下跌。2010年下半年许红和罗伯特卖掉了旧房子搬进了近3900平方尺的新房。 我愿意把它想成这里头包含了许红想让小她9岁的年轻丈夫高兴。许红大多的时间住在滨洲的家里,在北维这个新家呆的时间很少。身为工程师的罗伯特比较保守,觉得这一步跨的有点大。但许红为罗伯特喜欢这房子而高兴。也许这是一个能干的中国女性的见证。
196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红十四岁。那是向往大学对前途充满憧憬的时候,梦想却过早地破灭了。作为北京知青许红下乡到内蒙古。从那里她就不间断地与命运抗争,走到今天,落脚美国,成为终身教授。
2012新年除夕,我们就在许红的新家聚会迎接新年。周围一片漆黑寂静。她家是这个新居住区的唯一居民。此时房地产业还没复苏,一年多了,还没第二个买主。不过,没有害怕,开发商会把安全工作做足的。我玩笑罗伯特是无人国的国王。再过一年多,托泰森斯角(Tysons Corner)的福,这里的房地产好起来了。因为把泰森斯角变成一座新型城市的建设开始了,房价上涨。也证明买对了。预计到2050年,一座崭新的城市就会出现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离华盛顿首府13英里/21公里。
聊天中,许红问及我们有没有头痛,她近来常头痛。我说我偶尔会有头痛,但那是看电视电脑造成的。至于我先生从小就有头痛,那是一种强烈的疼。许红说她的疼没那么激烈。很少听到她提及病的事。说明这头疼令她担忧。但常听人说头疼,所以我没想过她的头疼会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我总觉得她的身体很好。转眼就要60岁了,可她的头发还是黑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健康的标志。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太大意了。她忽略自己身体发出的警告,没有尽早去看医生。
过了新年,与往常一样,许红开三个多小时的车回滨州上班去了。她和丈夫每个周末轮流开车去见对方。二十几年下来,我相信许红已经习惯了生活里拥有自己相当的空间。曾经也试图想在这周围找个工作,但终究没成。有人说,小别胜新婚。也许周末才见面的婚姻对他们俩是件好事。
2月12日晚9点左右,罗伯特来电话。他的声音很低沉。我知道他是个早睡早起的人。以往我们四人傍晚相聚的时候,到了9点他就犯困。此时这个钟点这般声音,我预感出了什么事。
"许红脑出血。"罗伯特说。
我脑子里试图将它与某种疾病挂钩。
"明天动手术。她得了脑瘤。我刚从医院回来。就想告你们一声以免万一。"罗伯特继续说。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然而,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消息还在后头。
原来一星期前的一天,许红在课堂上授课时,突然头疼难忍。于是去见了医生。不料想医生诊断为脑瘤,必须马上动手术。对于一个身体一直很好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许红说过她父母90多岁了,还健在。家族的健康基因让她自豪。可现在?"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这对她而言绝对是一个难以接受又残酷的事实。
第二天,罗伯特赶到许红那。打开脑部可是件大事。手术后自己还拥有正常的智力吗?许红表示了在当地医院做手术的担忧。于是,许红被推荐给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一间美国顶尖的医院。并且很快将手术安排在一个星期后。
也许这是她在人生里第一次把相当的精力放在学习工作以外的事情上。但不管她如何思考,决定,安排,担心或希望,都是紧紧围绕着工作这条轴在转的。约三十年下来,工作对她而言已不只是生活的保障,而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了。因此,脑瘤对她不只是对生命的威胁,还有对她脑功能的威胁从而导致无法从事她的工作的莫大担忧。人生大部分时间(相信超越8小时一天)都放在 工作上,以至于她不知道除了工作外,还会想做什么。
此时我们所有的人,我相信包括许红在内,都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手术上。而执刀医生竟是这个部门的头,很有名气。这给了许红和罗伯特不少安慰。他第一次见到罗伯特时,就给了罗伯特一本自己写的有关脑瘤的书。医院位于马里兰州。离我们住的地方约50英里,或83公里远。住院的这些日子里,罗伯特大多晚上在许红的病房里加张床过夜。早晨再回家。
和罗伯特谈下来,他觉得第二天由于麻醉的原因,许红大多时间会处于没有知觉的状态。所以我们决定第三天,也就是2月14日再去。但罗伯特保证第二天手术后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结果。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等待中的这一天过得特别慢。
我从没问过许红被推进手术室时的心理感受。我想应该是担忧与希望的混合吧。担忧被推出手术室后完全丧失了自己,包括不能左右自己的手脚;希望这一个手术后病除康复,生活如旧。因为这时的许红还没时间去深入了解自己的病。能有幸接受世界一流水平的治疗自然让她期望能跨过这个槛。至于我,从没接触过这样的病人,此时更是没想过这个槛会高不可逾。至于罗伯特,我想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多一些。因为她的姐姐和爸爸都不幸死于癌症。
和许多人一样,我知道癌是可怕的东西,但也听说许多人经过手术后都生存下来。所以,此时我的脑子里并没有把许红和"生命威胁"这样的字眼挂钩。只觉得正在走一个程序:入院—手术—出院—康复。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September 8, 2014
(I) 第二次放疗后
Susan Xu (许红)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按理她现在应该在校园里上班,可她却在我家。虽说她在宾州工作,可他丈夫却在北维州工作。丈夫这头他们的家离我们家大约四英里左右。5月16日2014年近中午时分,许红的爱尔兰意大利血统丈夫罗伯特将她送到我家。不想因去上班而将妻子独自留在家里。况且许红弟弟也嘱咐罗伯特不能将他姐姐一人留在家。晚饭后,罗伯特会接她回家。
罗伯特说昨天许红做完了最后一次放射治疗。也就是说,从2月初2012年她被诊断是脑癌(胶质瘤 Glioblastoma)至今,放射治疗彻底结束了。以后就只有每星期一次的注射及一些防止副作用的药物。而事实上,据她弟弟告诉我此次这个放疗应是6个星期,但现才4 个星期,医生已宣告结束了。理由我不清楚。接下来她的身体状况会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不得而知。比起4月14日一个月前我看到的她,状况的确差了很多。讲话表达失去了常人的能力;走路需要搀扶。但比之前她自己所描述的若接受第二次放疗她会变成"傻子",却好多了。她有对过去事情的记忆,只是对当前事情的记忆有较明显的减退。
为了避免这第二次放疗,她是那样的努力。她相信她的人生就是依靠努力走出来的。曾经就是这种努力,使她离开了她下乡的内蒙古成了大学生;又是这种努力,使她到了美国读完硕士和博士。这次她再次使用这种努力想跨过胶质瘤这个坎,以求得能继续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工作。因为她非常明白再来一次放疗,她就无法再工作了。况且跨过六十岁的她,还有她计划好的退休生活在前面等着她。
可这次不管她如何努力,现实却无比残酷。人生中第一次她感到她的努力是那样无济于事。癌是那样的刀枪不入,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过来,马上就要将她吞噬了。医生发出最后的通牒:再不做放疗,就只有两个月可活。丈夫也急了。终于她屈服了,同意做放疗。同时,整个心情下跌到了最低点,她明白这等于宣告了她 职业生涯的彻底结束。这两年零两个月里,她也不知哭了多少回。这一次她一定也哭了吧。两年来带着苦楚苦楚而激烈波动的心情不懈地努力,为的就是不要面对这种结局,可残酷的结局还是出现了。
两年多来,多少次的起起伏伏,眼泪与希望的交替。重复了多少回被推上浪尖,刚看到附近有个小岛,就又被狠狠地摔进漩涡里。每次MRI(磁共振成像)的结果显示没有变化,都能让她有所兴奋,给她带来一线希望。随即全力以赴去争取。但下一张MRI报告却有了新的负面的变化,再次将她抛进绝望中。如此反复,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折磨!然而,两年多里,她以主动的态度去学习理解与自己病情有关的知识,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案,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决定。我想她已以最佳的方式走过这段艰难的旅程。她以积极拼搏的态度击败了医生给她的只能活一年的预言。她以主动争取的行动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过正常人生活"的日子。
虽说她现在被放疗和药物摧残得体力不支,但很明显,她又在做着另一个努力。那就是很努力地吃饭。几十年下来,努力成了她的一种习惯,习惯演变为自然。自然是强大的,它可以毫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只要在她的前方有希望的火焰在闪烁,哪怕那火焰很微弱,她也会立即表现出她的努力。她希望通过努力地吃饭,能改善自己的体力状况。我也对她产生一种新的希望,那就是过些日子,她能强壮起来。恶化到这个地步,一直是我没想象过的。读了个别胶质瘤患者最终存活了十几年二十年的例子,我总觉得,或说是在幻想许红也会是属于这种状况。完全忽视她这种肿瘤的平均存活率是1.4年这样的统计数据;也不知很多人在半年内就走人了。也许… 也许虽然如今她失去了生活的质量,但她接下来的日子还能以年计算。也许… 也许我又在幻想;也许… 也许我希望或相信有奇迹…
三天后,5月19日,她丈夫再次把她送到我这。可她的体力却明显不如3天前。虽然在罗伯特的鼓励下,她缓慢而艰难地走完了我家门前的十一级楼梯加一级门槛,但她却不愿再走门内的6级楼梯了。她瘫坐在楼梯上不动了。想想之前她来过我们家无数次,这些楼梯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对她而言,这些楼梯竟成了半座珠穆朗玛峰。我突然感到我的脑子还不知怎样处理适应这种变化。我发现当心里拒绝相信的时候,那种抵制的力量是极其顽固而持久的。
我问她: "你在想什么?"
她说:"想我的将来啊。"
我顿时为她燃起一线希望。我想她知道自己不能回滨州授课了,所以在盘算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说明她此刻没有处于最后的绝望。
我让她就坐在楼梯上吃午饭:"吃完它,能长点力气。"我说。"你会慢慢好转的。"
她精神一振问道:"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才感到其实她不抱希望。但她很希望听到别人的鼓励。换作以前,我会认为即使不是真的,我也应该说是的。在治疗方面,许红喜欢美国的先进;但在语言方面,她喜欢中国式的婉转温和含蓄。可现在的我受了西方文化影响后夹在两种文化中,也不知道这么说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虽然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期望也是这么认为的。
傍晚,我们留住罗伯特吃完晚饭后才带许红回去。罗伯特对许红说了几次该离开了。许红说到沙发上去坐。这让我联想起她没病之前,有多少次我们四人坐在沙发上聊天。快到9点时罗伯特就会开始打哈欠。他是个早起早睡的人。可许红还没有睡意,不太想走。也许第二次放疗对她有伤害,但她还是以前的许红。
离开之前,她叫了一声我先生的名字,给了一个带着特别眼神的微笑。她的微笑和眼神在我看来好像在说"我曾经也与你同一个级别(博士)",对今晚他们俩个男人如同以往的政治话题,自己却无法像以往那样插上话而感到尴尬又无可奈何。那神态隐含着几分的凄楚。对自己的脑子,如她之前所预见的,已被伤害而变"傻"这一点,她还是有意识的。这对一个要强的人来说,是何等的一种失落感和落差感!她那么那么地努力,就是为了要避免如今这种状态,可终究还是无奈地走到这一步。
(II) 两年多前
近十几年来,我们大部分的新年是在许红的旧房子度过的。许红,罗伯特和我先生毕业于同一个大学。2008年美国房地产业危机,房价下跌。2010年下半年许红和罗伯特卖掉了旧房子搬进了近3900平方尺的新房。 我愿意把它想成这里头包含了许红想让小她9岁的年轻丈夫高兴。许红大多的时间住在滨洲的家里,在北维这个新家呆的时间很少。身为工程师的罗伯特比较保守,觉得这一步跨的有点大。但许红为罗伯特喜欢这房子而高兴。也许这是一个能干的中国女性的见证。
X
XU ping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July 14, 2014
Susan,
We are proud of you and remember you for ever. We will tell our daughter Chris about you and your story. We love you.
Your sister Ping and Yadi
Z
Zuoying Xy posted a condolence
Sunday, July 13, 2014
Xu Hong is one of my two sisters; we used to play together in childhood. Her talent became apparent when she was selected by China Ministry of Railways for post-graduate study in the US. Since obtained her doctorate in RPI, she had been successful as a researcher and teacher in Penn State Univ. But the turning point in her life is when she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her Savior on Oct. 27, 2013. Her faith made her strong during her last days. The last days were really difficult for her - she became weaker and weaker physically such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her even to talk. But she prayed to the Lord to give her strength. Praise our Lord, for He gave Xu Hong strength to walk during her last days. she always said to me "I am fine", and was concerned about my well-being when she was enduring the pain. So she became weaker and weaker physically, but was strong in the Spirit of God.
Personal I own my sister a lot - she helped me to come to study in the US, and continued to help me when I was in difficult times. But I am only one of the many whom she had helped. A light has gone out, but she will be greatly missed by everyone who knew and loved her.
Xu Zuoying, the borther
W
Wei Zhou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8, 2014
又过了很多年,2003年夏天,我们全家去DC旅游,受到左英(许红弟弟)和许红的热情接待。第二年,许红去丹佛开会,顺便看望我们。她给我的印象是:时过境迁,笑容依旧。记得在许红DC家里,我女儿因为与弟弟下棋输了哭起来,许红安慰她说:"很多年后,人们记得你决不会是因为输了一盘棋"。
After many years, we met her again in 2003 when we toured DC. We had a good time with Xu Hong and Zuoying. The year after, she went to visit me when she wa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Denver, Colorado. Xu Hong, the same smile although a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ed different lives.
许红安息,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你的辉煌人生,你的微笑!
Rest in peace! We forever remember you, Xu Hong, your life and your smile!
W
Wei Zhou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8, 2014
许红是大姨婆(即外婆的大姐)的小女儿(方烨表姨)的小女儿,生前是宾夕法尼亚州大商学院教授。我与许红表姐只有几次接触,就像看到流星一样,短斩却难忘。
Xu Hong and I are second cousins. Although I only met her a few times, it was like meteorite, instant but forever.
第一次是文革后期,在北京的亲戚们开始来往。妈妈说这是因为文革中大家都受到调查、挨整的结果。就这样,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来往。那是在我们家小酱坊胡同22号拥挤的一间平房里,妈妈为我们举办了一个聚会。有很多亲友,许红也来了,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很漂亮、精神、自信,见人就笑。许红因事提前离开,留下让我铭记一生的微笑。
The first time was the later stage of the so-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Relatives in Beijing started visiting each other, as a result of common experi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ur generation also started befriend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party at our crowded home, many second cousins came, including Xu Hong. She was so beautiful and confident, smiled all the time. She had to leave first and left us with her forever sweet smile.
第二次大概是1986年前后,我、绳百还有郁彬(四姨婆的孙女)在加大伯克莱分校读书,许红当时在东部伦斯勒理工学院(即绳百和我现在工作的大学)读书,来参加学术会议。许多年过去,凭着对她微笑的记忆,我一下认出她来,不同的服饰和国度,同样的微笑!记得我刚拿到驾照,居然斗胆开车带她游逛旧金山。回来后我庆幸没出车祸,许红夸我车开得好,给我不少自信。后来郁彬也来了,绳百为我们三个表姐妹拍下历史性的合影。
The second time was around 1986 when Shengbai, Bin Yu, and myself, all second cousins, were studying at UC Berkeley while Xu Hong was studying at RPI. She came here for an academic conference. After many years, I immediately recognized her from the familiar smile. Having just obtained driver's license, I was brave to take her tour San Francisco. I was nervous but she was calm and praised me, which enhanced my confidence. After Bin Yu came, Shengbai then took a picture of us (from left) me, Xu Hong, and Bin Yu.
J
Jessica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8, 2014
丧礼结束了,很难想象许红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多少原来并不显著的记忆不断在脑海里涌现。今年5/19,罗伯特把许红送到我们家。我以为许红以后可以经常到我家来。没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次。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傍晚吃完饭后,罗伯特叫许红走。许红说到沙发上去坐。这让我联想起她没病之前,有多少次我们四人坐在沙发上聊天,快到9点罗伯特就会开始打哈欠。他是个早起早睡的人。可许红还没有睡意,不太想走。也许第二次放疗对她有伤害,但她还是以前的许红。我跟她说她还会再来的。真没想到她再也来不了了。想起那天她的一个反应,不免有点心酸。我告诉她把午饭吃完了能长力气,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请神一振,问我:"You think so?"说实在,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的。不然第二次放疗不就失去它的意义吗。没想到,只有一个半月,她就撒手人间。想想原本在那里的一个大活人,怎么瞬间就不在了。生命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但她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她对有关资料作了很彻底的搜寻。她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所有选择。她为自己的选择奋力而战到最后一刻不后悔。她的这种精神继续存活。
The funeral ended. It is hard to phantom she is not around anymore. So many insignificant memories come back now. May 19, 2014, her husband sent her to our house. And I thought she would come often since. I couldn't believe that was the last time. She was deliberating since. After dinner, her husband told her they should leave. Xu said she was going to sit on the sofa. It triggered my memories. Before she was sick, so many times four of us sit on the sofa, talking. About 9pm, her husband began to yawn. He is the kind who goes to bed early and gets up early. But Xu Hong was not sleepy and didn't want to leave yet. Maybe the second radiation had done her some damage, but she was still the same old Xu Hong. Thinking the one reaction she had that day, I felt sad. I told her: "Finish the lunch, so you'll gain some strength. You'll get better." Lighten up by my words, she asked: "You think so?" Honestly, I really thought so at that time. Otherwise it defeated the purpose of the 2nd radiation. Unexpectedly, only one and half months later, she was gone. Imagine she was there a minute ago, and next minute she was forever gone. How delicate a life is!
But she had put up a good fight for her life. She had done a thorough search and well understood all the options she had. She fought hard for her choice and had no regret. Her spirit stays and lives on.
C
Cheng Nie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July 7, 2014
Dear Professor Xu,
Stochastic Process (2011 Spring) and Dynamic Programming (2012 Spring) are two of the best courses that I have taken at Penn State. In the very first session of the Stochastic Process, you asked us to do a self-introduction to let our peer students know who we were and why we decided to register for the course. I said "I register because the course is in my first-year qualifying exams." You laughed out loudly probably because you have never heard a more blunt answer. In the 2012 Spring, I started taking your Dynamic Programming course while worked as a TA for you in the Stochastic Process couse since you were teaching both courses in the same semester. You asked us to do another self-introduction and I said "I had great review from the Stochastic Process class you gave the previous year. You are a great teacher and I decided to register even though this course is not mandatory." Unfortunately, you did not finish this course due to the disease.
I still remember that you need to teach both classes the same afternoon. You apologized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class that you had to sit to instruct that day because you did not feel well. Then we all heard the bad news of the brain tumor and your classes have to be canceled several weeks before two Professors from IE department resumed both classes. I do not know how the other class went, but for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clas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was way better with you as our professor.
You treated us a good lunch when you saw me and my wife together at the Panda Express in the HUB of Penn State. We had a great dinner in Fuji and Jade Garden and a great party at your State College home watching an NBA game (Celtics vs Heat) to celebrate Jay and Justin's wonderful placement. You had many cards in display in the living room and I remembered that one of card was from your husband and it reads "Thank you for those wonderful moments." I showed it to my wife and we looked at each other with love.
I am lucky to know you at Penn State. May you will rest in peace.
Best,
Cheng
H
He Kaifen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July 7, 2014
盯着邮件上那个刺眼的词,我迟迟回不过神来,无法把"funeral"与后面那个名字联系起来,在我心里,那是一个甜甜的却倔犟的、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女孩,我们表姐妹中的佼佼者。
那一年,5岁的红红跟着她母亲——我妈妈的小妹妹,我们叫她小阿姨——到我们家来玩,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非常可爱。我用双手从腋窝处将她托起,在狭窄的房间里转圈圈,不料,抡起来的两条小腿重重地撞在铁制的床架上。我自知闯了祸,准备迎接一场风暴。但红红竟连一声都没哼,只有那双大眼睛,汪满了泪。一个才5岁的孩子,上苍赋予她如此坚强的性格,是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坎坷人生吗?
那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那一代孩子,更是生活还没有起步,就被抛向了深渊。文革开始时,红红才14岁,刚读完初一,顷刻间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关牛棚,哥哥惨遭不测。无法想象一个稚嫩的女孩,怎么能承受这样的重击。后来,冠以知青称号的那一代,陆续被送往农村,她和姐姐许梅自然也不能幸免,姐姐在东北,她在内蒙。兵团还是插队?我没有听她们述说过自己是怎样走过那段本该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的。但她们的同龄人曾对我描述过那时的生活:在东北,掰棒子时节已需要穿棉服,太阳升起,衣裤被露水打得透湿,到收工时,它们已冻成了冰筒筒;一个人每月2钱油,月初发油票,知青点的男孩女孩聚在一起,炸一次油饼,这个月余下的日子,就只有清水煮白菜了…。
茫茫人生,希望在哪里?几年过去,红红所在的那个知青点,人已经走得稀稀落落,参军的、病退的,有办法的全离开了。不可能再呆下去。据我母亲说,有一阶段,红红常到她家——那里离西尧表舅家很近——总是坐到晚上10点11点,再去等侯忙得焦头烂额深夜才归家的西尧表舅。就这样,红红来到一个部队造纸厂,"全是随军家属,大妈大嫂。"没多久,她毅然离开了这个可以混日子的地方,回到了农村,"在这里,至少我还有知青身份,"她说。那时,黑暗中已依稀露出一丝朦胧的光,要招收工农兵学员了,她要争取这个机会,靠实力拼出一条自己的路。
文革期间的大学,为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打了怎样的基础,我不清楚。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大学看到过为这些学员编写的微积分教程,也许可以窥得一斑。记得教程上那一段段顺口溜式的句子,让人忍俊不禁:从线到点求微分,从点到线求积分;从面到线求微分,从线到面求积分;从体到面求微分, …。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这样的教材不足为怪。想要学到真本领,全凭个人努力。大学毕业,红红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加减乘除就能应付",她不甘心沉溺于这样的生活,也知道大学的基础远远不够,开始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学习,提高自己。"光数学题就做了厚厚的九大本",小阿姨后来告诉我。生性喜欢在知识海洋中游泳的她,开始寻找发展的机会。在把这些习题集拿给北方交大的老师们看时,他们惊讶了:"有些题目,我们都没见过。"是她自己做的吗?在严格考核考试之后,红红走上了大学讲坛,跨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1982年在教育部举办的出国人员培训班上,我遇见红红,笑容灿烂,显得自信而轻松。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战胜多少竞争者,她才得以在英语笔试与听力测试中脱颖而出。自此,红红迈上了新的人生台阶,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在留学生中,她的聪颖与善良,诚恳与正直,使她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喜爱。记得有一年,西尧表舅——访美期间他见到红红——说:许红可真了不得!找她谈话都得排队呢!
红红去美国以后,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只是欣喜地知道,这些年,她登上了一座比一座更高的山峰,从硕士、博士,到被美国著名大学聘用,成为终身教授。一个14岁就被迫辍学的女孩,这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不言放弃,从不向命运低头。
世纪之初,我到美国开会,临离开前到她在华盛顿的家。车开错了路,到达时已经5点多了,红红在等我们。吃过饭,很晚了,她还要风尘仆仆地开几个钟头车回宾州的学校。晚上,我睡在客房里,整洁、素净,花瓶里插了一支向日葵,花如其人,高雅却平实。
听说她得病,我非常震惊,责怪上苍的不公。我知道这个病的凶险,两个朋友家的病例,都没有超过半年。红红尽了最大努力去抗争,两年多,已是奇迹。听小阿姨说,去年,病重期间,她还参加博士生的答辩会,因为有越洋的时差,在京的她需要在夜间工作。
我未能见到她,返京时,红红已经回美国了。两年前,我在小女儿家小住,大女儿来度假,曾提议一起去看望她的红红阿姨,她得到过她的帮助,心存感激。未能成行,怪我,总觉得来日方长,还有的是机会。现在后悔不及。
说是红红皈依了基督,这一次,她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召唤。10日,许梅与妹妹通话,她已极度虚弱。当天,许梅做了一个梦:她自己和爸爸妈妈一同攀爬一个有很多台阶的高地,去看红红,抬眼望去,上方是湛蓝的天空,无比的光亮 … 。那是红红人生经历的隐喻吧!在梦里,姐姐没能见到妹妹,她一定已登到了更高的地方,或许,正静静地安睡在上帝的怀抱,或许,又开始了新的升华。
//凯芬
W
Wang's Family posted a condolence
Monday, July 7, 2014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don't want to happen but have to accept, things we don't want to know but have to learn ... Xu Hong sister, you should always know, wherever you may go,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we will never be far away. Those we love don't go away, you walk beside us every day, unseen, unheard, but always near. Jianlin, Weilin, Honglin, Linglin, Donglin
H
Hui ZHAO posted a condolence
Sunday, July 6, 2014
Before I joined Smeal, Susan was a respected senior faculty to me. Then we became colleagues, coauthors, and close friends. During the close-to-two years I have been here, I witnessed her battling cancer in perseverance and hope, with the highlights of putting her trust into Jesus last summer and being baptized last fall. She was a proactive patient, reading, seeking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her treatment plan. We frequently prayed together, counting blessings and seeking guidance. In the ups and downs, we used the most familiar dynamic programming concept to talk about how God personally and dynamically guides us. Susan loved research. Even in her search for treatment options, she frequently reflected upon and discussed with me how the clinical trial systems were and how they could be improved. That inspired us to start a new project. At one point, she even thought, Lord willing, her best research, which would use her knowledge gained from her own patient experiences, was yet to come. Yet, God had a different plan. 10 days before her passing, we went to see her, she was weak, but still conscious. We sang hymns, reading verses, and prayed together. Today, though it hurts to lose a colleague and friend, I know she has rested from her hard work in this world and moved on to a better place to be with Jesus. I know I will be there to see her one day. Bye for now, sister.
- Hui ZHAO (7/6/14)
D
Duncan Fong and Mosuk Chow posted a condolence
Sunday, July 6, 2014
For over a quarter century, we are colleagues and friends. Your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always impress us. In addition to your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you take good care of your students. You are a true scholar. We miss you!
M
Mr. David M. and Dr. Jamie A. Imlay posted a condolence
Sunday, July 6, 2014
Bob, Our heartfelt deepest sympathy to you and your family at this difficult time. May the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you have live with you in your heart forever. Keeping you in our prayers.
H
Harihara Natarajan posted a condolence
Saturday, July 5, 2014
Harihara Natarajan purchased flowers (The FTD Golden Memories Arrangement - Standard)
Dear Robert, Please accept my deepest condolences. I am very sorry for your loss. I am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of Susan's passing.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being in her class, of working with her, of hanging out with her at conferences, and of being moved by her spirit even as she fought this disease. She was an invaluable resource for me, a well of sage advice to draw from; I will miss her a lot and cherish the time that I spent with her. May she rest in peace.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you. Best, Hari
W
Weicheng Shen and Jessica Chen posted a condolence
Saturday, July 5, 2014
Together, we dined in restaurants, strolled in the parks, enjoyed Alaska cruise… Xu Hong, we’ll cherish those memories. And we’ll always miss you.
A
Akhil Kumar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Akhil Kumar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With deepest sympathies. I will miss Susan very much. She was a dear friend and valued colleague for many years. May she find peace.
H
Huaye Zhang, Yiwei, Frank and Claire Duan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Huaye Zhang, Yiwei, Frank and Claire Duan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We are deeply saddened by the passing of Aunt Xu Hong. Please accept our most sincere condolences.
H
He Kaifen and Zhang Shengji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He Kaifen and Zhang Shengji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We love Xu Hong. She will forever be in our hearts.
J
Jinghong, Johan and Celia Sundell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Jinghong, Johan and Celia Sundell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We are very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loss. From our family to yours, our most heartfelt sympathies.
J
Jiangxia Liu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Jiangxia Liu made a donation to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INC
We are very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loss. From our family to yours, our most heartfelt sympathies.
K
Kuzu Family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Kuzu Family made a donation to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INC
We are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our mentor and friend. She will always be in our prayers. Please accept our condolences.
Y
Yannan (Lily) Shen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Yannan (Lily) Shen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e passing of Dr. Xu. She was the PhD director of Smeal who signed my offer letter and welcomed me into Smeal in Fall 2011. Susan was always kind and approachable. I will forever remember her warm smiles and encouraging guidances in my heart.
W
Wang's Family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Wang's Family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Xu Hong sister has a special place in our hearts,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er and treasure the memories we had with her.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most heartfelt sympathies. Love, Wang's Family (Jay Wang; Weilin Wang and Yan Zhang; Honglin Wang and Weixing; Linglin Hennessey and Jim Hennessey; Fuying Wang)
D
Duncan Fong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Duncan Fong made a donation to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IN RICHMOND
H
Hiroko Okajima posted a condolence
Tuesday, July 1, 2014
Hiroko Okajima made a donation to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INC
I am deeply saddened and shocked by the passing of my mentor Dr. Susan Xu. She made a tremendous impact in my life as I became her student. She spent so many hours helping me finish my Ph.D. and cared about my husband even after she became ill. She was a great researcher and wonderful woman. I will always remember her kindness. Always in my heart.